【書評‧文學史】王德威/海峽中線,就是文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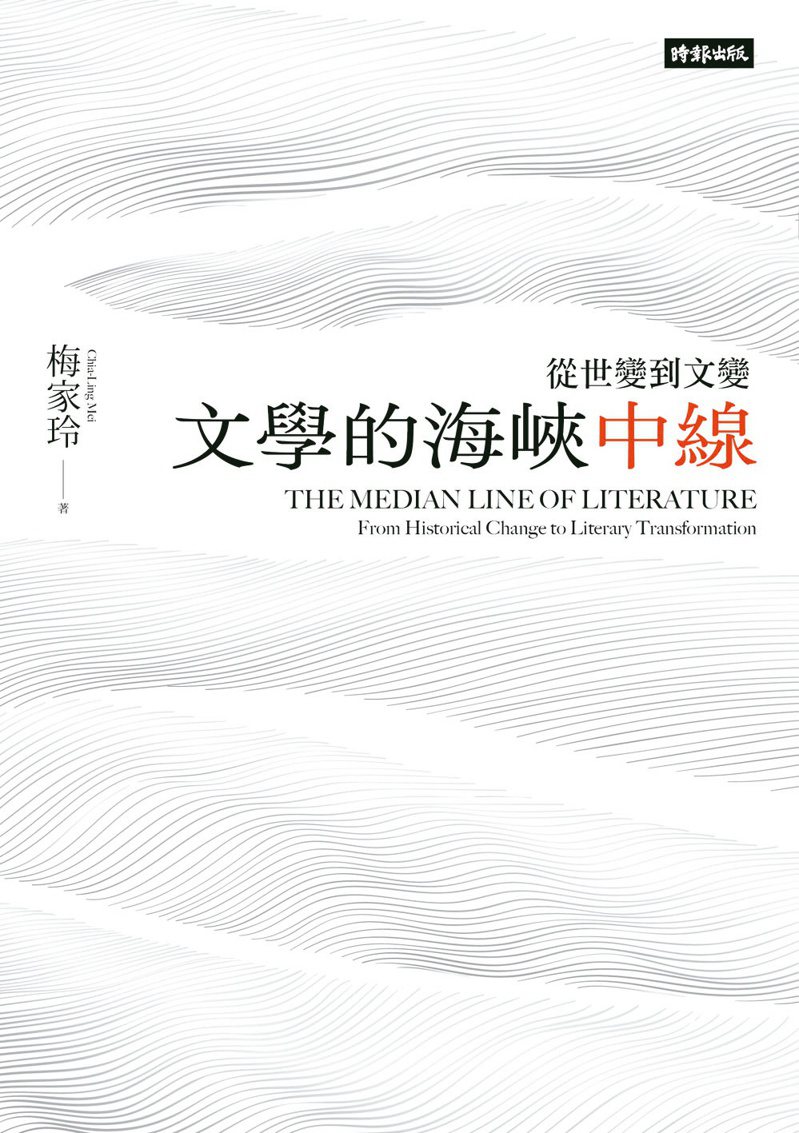
《文学的海峡中线:从世变到文变》书影。(图/时报出版提供)
推荐书:梅家玲《文学的海峡中线:从世变到文变》(时报出版)
一九四九年后现代中国文学一分为二
「海峡中线」是台湾海峡中的一条无形界线,东北─西南走向,长度约五百公里。中线的设定始于一九五四年台湾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方为控制国共对峙局面,要求国军必须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活动,自此台湾空军即以「海峡中线」规画防空识别区。
中共政权既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然不承认中线存在。然而在冷战格局中,这条中线却发挥相当作用。两岸一九五、六○年代屡有军事冲突,之后紧张局势趋缓,不跨越中线成为双方默契。二十世纪末以来台湾政局变换,中线问题又成焦点。二○二二年夏天台湾与美国互动关系热络,八月初解放军围绕台湾军事演习,越过中线,至今已成为常态。
文学与海峡中线有什么关系?这条在地图上由北纬二十七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延伸至北纬二十三度、东经一一八度的虚拟直线,是由美军势力主导,以军事制约为前提的「互不侵犯的假想中线」,中共称之为「伪命题」。然而不论是虚拟、假想,或是伪命题,中线的确在历史时刻中发挥作用,维持海峡两岸起码的和平。
假作真时真亦假,道是有时恰似无。海峡中线不像东西柏林森严血腥的围墙,也不像南北韩危机四伏的三十八度线。在波澜汹涌的水道中,它间接靠航海与卫星仪器确定方位。中线是一个象征符号,甚至隐喻,演绎二十世纪中期一段波诡云谲的政治叙事。中线虽为虚构,但落实其「存在」的军事角力和外交运作却无时或已。跨越与否的凶险和结果成为不断揣测、协商的前提。在想像与实存、修辞与政治、拓扑与疆域间,海峡中线既划分又连接两端,出虚入实──就是一种「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领域是否也有一道海峡中线呢?这是梅家玲教授新书《文学的海峡中线:从世变到文变》的重点。一九四九年后现代中国文学一分为二,各自形成论述。早在一九二○年代共产党已经发展文学的革命功能,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高举工农兵大旗,强调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革命成功后,毛对文学的操弄变本加厉,各种清算运动每每从文学开始,可见一斑。
相形之下,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摇摆得多,早期一面认同五四新文艺启蒙,一面自许为正统传人,一面向往苏联式文艺机器,企图控制「上层建筑」。国民党政权来台后痛定思痛,认定五四新文学为动摇国本的乱源之一,因此多所压制,同时在「大中国」前提下,对本土文学传统视若无睹。反共抗俄成为文学使命。
然而有心之士,不论本地文人或新近渡海而来者,坚持以文字铭刻所思所闻,居然创造出奇花异果。一九六○年代之交现代主义、乡土文学兴起,各自将台湾文学导向不同方位。八○年代末以来台湾本土意识崛起。台湾文学又经历一次洗礼,如何与中国区隔成为又一代学者文人念兹在兹的课题。
据此,两岸文学可谓泾渭分明。跨越中线与否仿佛看不见的攻防,战争与和平,民主与极权,故土与离散,正统与嬗变这些命题都将遭受考验。然而两者论述其实暗通款曲,都是以国家主义绑定文学叙事,而国家文学又是十九世纪西方国族主义论述透过日本转口中国的舶来品。换个角度思考,两岸对文学与个人、社会、国家所做的有机连锁,何尝不正是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从「文章经国之大业」到「兴、观、群、怨」,老中国「文」与「政」的纠缠历久而弥新。
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在台湾灵根自植的一页
梅家玲教授的《文学的海峡中线》以二十世纪中期以降为背景,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在台湾灵根自植的一页。她不仅视海峡中线为军事座标,标明世纪中期两岸分立的事实,也视其为一种感觉结构,投射国家危机或转机的临界点。值得深思的是,梅教授的研究点出「文学的海峡中线」其实变动不居。因应时代政治氛围,它可以是反共的,也可以是反中的;可以是延续古典、一以贯之的,也可以是落地生根、自成一统的;可以是写实主义的,也可以是现代主义的,可以是历史的先入为主,也可以是历史的后见之明。
这引入此书的另一个重点。既然文学的海峡中线未必总一清二楚;文学生产与诠释也未必总如应斯响。台湾乡土文学标榜的模拟式写实难道没有大陆乡土文学的影子?现代主义到底是去政治化还是再政治化的美学实验?反共文学的八股何以与共产文学八股似曾相识?文学史是文学对国族历史的复写,是文学脱离或陷入「国家」束缚的纪录,还是作家各行其是的见证?
本书透过文学史书写、国、语、文辩证,国文教科书编纂、文学期刊的推出,还有大学(尤其是文学系所)作为教育机构,对以上各种观察做出回应。全书共分为六章,首先以二十世纪中期两位文学学者黄得时与台静农的文学史书写,点出「中国文学」到台湾的微妙变迁。黄得时(一九○九─一九九九)成长于殖民时期的台湾,大学期间即展现文学热忱,积极投入各式文艺活动,一九四三年发表〈台湾文学史序说〉,为日后〈台湾文学史〉书写首开其端。黄所论述的「台湾文学」以明清之际沈光文渡海来台,成立「东吟诗社」推广文运为起点,不仅将此后宦游来台的清代文人之作纳入文学史,更认为「康熙雍正时代的儒学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场」。
正当黄得时等在地知识分子自觉酝酿台湾文史脉络的同时,一辈大陆文人学者渡海而来,台静农、许寿裳、魏建功、夏济安、英千里、殷海光等都先后参与台湾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过程。其中台静农(一九○二─一九九○)的案例尤其特殊。台早年厕身左翼运动,与鲁迅来往;抗战后因缘际会来台,任台大中文系主任长达二十年。由于国共局势使然,他对早年经历讳莫如深。但所着《中国文学史》却透露曲折线索,让我们得以一窥其人心事。
梅教授提醒读者,黄得时、台静农的文学史书写一方面各有所本,一方面也分享当时流传的泰纳(Hippolyte Taine)文学史观。泰纳以「种族、环境、时代」作为衡量文学、历史、国家联动关系的方法,在在显示十九世纪欧洲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文学成为现实的简单反映。黄、台虽然承袭此说,却各有修订。黄对台湾历史记忆频频致意,台则对中国文学的形式与寄托别有领悟。他们怀抱的「史识」与「诗心」毕竟注记了个人的块垒。
重点转向文学知识生产的场域
其次,梅教授将重点转向文学知识生产的场域,检视文学如何透过「国语」和「国文」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一如「国家文学史」,「国语」与「国文」也是经由日本输入晚清,进而落实为各级学校的文化实践。两者都脱胎于十九世纪国族主义「言文合一」运动。据此,白话被视为纯洁透明的表意工具,直通文字、文化,以迄民族国家精神;文言则被视为传统图腾,装点封建菁英的教养和趣味。这一「言文合一」的诉求又被左翼运动放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器。其极致处,一九三○年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等人甚至提倡汉字拉丁化运动,彻底废除中文。
诚如梅家玲指出,「语」与「文」是相对概念,二者的辩证交融,原是持续发生的自然现象。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方言杂陈,原无统一的「标准语」。反倒是自秦汉以来即已统一的「文」,不仅成为境内交流沟通的重要凭借,甚至远播东亚,形成「汉字文化圈」。唯「文」须经学习而得之,仅能流通于士人阶层,一般庶民难以亲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订定「国语」,以利全民沟通,更企图普及教育,进一步打造「国文」,形塑全民「共同体」。如此一来,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成为「『国』文」的过程中,平添争议。
不少台湾学者倡导台湾话与台湾文的独立性,却不自觉地发扬五四时代由胡适、陈独秀等所推动的白话运动。他们的言文合一理想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继承而非拒绝了五四、甚至中共左翼传统。更反讽的是,推动台语拉丁化的学者同时与帝国殖民及列宁左翼语言策略形成应对,仿佛经由文字语言的统一操作,摆脱杂质,即可形成有效政教机制。近年的文白之争仍然延续此一辩论,梅教授的研究因此特别值得玩味。
梅家玲的国语文探源学也为当下大学国文课的存废之争提供又一省思角度。如果国文攸关国家想像共同体的建立,提议废除者必须扪心自问,他们是期待将语文教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脱钩,解放文学的多义性;或是改头换面,将国语文教学置于另一套国家民族主义的框架,继续国/文的正当性;或是仅仅现学现卖,追求语文的实用性?
梅家玲的回应之道是重建历史脉络,审视一九四○年代以来郭绍虞、魏建功、朱自清、杨振声等学者在不同语境所编纂的国文教材。文言还是白话?实用还是修养?认同还是反认同?这些辩论非自今始,唯有明白了「国文」本身的前世今生,继之而起的辩论才能切中要害。「国文」课程、内容和教学法当然有与时俱进的必要,如果仅操弄国/文转型正义,不过将时钟拨回到百年前的「文学革命」时刻,将原本千丝万缕的「传统」简化为铁板一块。至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在AI时代不是有点落伍了?(上)










